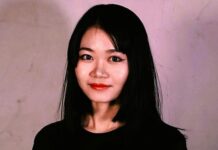關於工作與生活,能帶上舒適色彩最好,適合了就愉悅,不適合就由時間輪回重生,萬物總是這樣的。
遐想是遠方,是出行。這是我在煙花人間最樸素的欲望,哪怕去趟省會。曾經聽人講,鄉里人週末進縣,縣裡的人週末進市,市里人週末進省,這些都是趕集般興奮的。我所在的城市最便捷的就是去省會,高鐵一個鐘頭輕輕鬆松的就能換個新環境。
幼時和父母在上海都市的慢生活,印象一直深刻,以致於現在不管工作生活再忙碌,一但想休息第一選擇就是外出,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去。外出一定要坐火車,高速列車才像外出。咣當咣當的聲音總是讓人想起童年,那準備行囊的忙碌和興奮,母親準備行程零食的儀式感。有次在探親的火車上,默默望著窗外,感慨如兩條無限延伸的鐵道。
我希望我找到自己的。或者就坐高大的越野車,去真正的戶外出行。
坐上高大的越野去西藏滌蕩靈魂,是對同學們失約後的調侃。一直沒有機會實現這些,但肯定會實現,畢竟這是決定要去做的事情,為自己而做的事,人的一生又能有多少次是為了自己。去不了西藏就勇敢的去趟西雙版納吧。在疫情初期近乎窒息的壓抑感下,面對空城的淒涼和當時無助惶恐的目光,網上雜亂的唇槍舌戰,目及信念堅守大無畏的衛士後,無限感慨。像生命的呼吸和最後的掙扎。
疫情緩解,一開放,我毫不猶豫的就飛過去,在布朗山下一友人親戚的農莊住下來,對面就是小布朗山,右邊山腳下就是緬甸了。陪我的大姐每日的愉悅也讓我愉悅。 那樣的日子是詩。每天大量的詩句在布朗山頂的薄霧中湧現,在茶山的春天中旋轉。
我寫每片葉子,寫大山,寫傣族人的歡笑,寫布朗的星空明月,寫納西族的愛情,甚至寫下夜晚幼時數著入眠的小白兔。忠實的讀者網上的友人,他們關注著我每日對山上少數民族生活的描述,山寨裡潑水節的歌唱,家家戶戶特色的美食。當然,他們也不停緊張的教我自我保護的技巧,講緬甸邊境的複雜,每天都詢問,好像我時刻有被綁架的危險。
但我的目光所至皆是美好,那些善良純樸的山民,那些濕潤的潔淨剔透的清晨,那些歡快的歌舞,大聲的號子,那些美麗的傣族姑娘,納西族人的純樸,在這裡能找到回歸與重生。友人們此生或許不會有機會到這些山寨,或許來過也找不到我筆下描述的感覺,因為那是當時的,是專屬我的,我的現在進行式是神話,具有神秘性。
終於坐上越野進山。是在兩位有常年戶外經驗的朋友帶領下。友兄和友妹準備帳篷和各種小物件,我傻傻的不知道該拿什麼,拎個旅行箱和零食袋到了車前。一陣大笑後,大家說我開創了戶外拿旅行箱出行的歷史。原來戶外越野行李必須是輕便軟裝的,這樣才能變魔術似的從越野車上拿出一個又一個用品。
友妹告訴我,玩戶外不問每個人舊往和出處,大家就是同行夥伴,同甘共苦。我們搭起帳篷聽著雨聲,與另外的團隊聚在一個地方,分鍋點灶做飯。友兄說,野外最重要的是水,不要像在家一樣的洗漱和浪費,但是可以喝茶。我帶來的用品只有旅行茶具能服務大家,但是也終於在這個團隊中,有了歸屬感;還有一次到了山頂,是和本地玩越野名氣很大,去過無人區的兄長們,他們讓我看到了另一個世界。
在雜亂的樹叢,坎坷的山路上,越野車在崎嶇不平中執著的行進著。休憩時,在寧靜的山頂,大家有時聊天,有時沉默的看著夜色或遠方。我看到星空,彷若看到每個生命永存的光亮,每個光亮都是自由的秘密,毋須懂得,只要有光。月夜星空的帳篷內,我急急寫下詩句,紀念這些閃光的生命,內心充滿敬意。
越野就是無路時堅韌的尋求突破。毋須理由,由心出發。佩索阿的《不安之書》上說過,一個袒露的靈魂,是各自的哲學宇宙;我認為,真實是生活與生命彼此的尊重。
海德格爾說詩作中的「如此輕柔」是滑行。輕柔之物就是滑離的東西。夏天滑入秋天,滑入年歲的傍晚,也滑入一個溫甜的夢;希望就是留存美的一切印象,思索被遺忘的,那從寂靜之庇所中召喚出來的,因而自行澄亮的聲響,原本就是光亮。
依然喜愛茶台前的蘭,清冷微笑著看到纖嫩綠色的枝葉就足夠了,它的靈魂我能看到。是溫厚的。
延伸閱讀
- 緬甸茵萊湖:空性的水上生活
- 向海而學:從容來去有度的生態智慧
- 港漂生態:味覺涅槃或者精神游牧
- 南昆山上看翠竹:層層疊放一望無垠
- 鯨魚之淚:那屬於深藍的真正的史詩
- 昆蟲誌:螻蟻、飛螢、壁虎、斑蝶
- 徒步於緬甸昔卜:尋找世間美好樂園
- 人在大別山:一次山間行旅中的書寫
- 阿勒泰白樺林:大地深處編織的詩章
- 橄欖客棧:一簍青橄欖與兩張老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