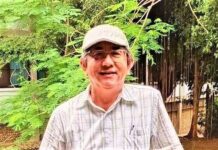那滴淚,是看不見的。
它不從眼角滑落,不在臉頰上留下濕潤的痕跡。它凝結在每一次遲滯的轉身裡,回盪在每一次探出水面、為換取幾條小魚而發出的空洞哨音中。它是一首被囚禁於水泥池中的、遼闊的史詩,無聲地蒸發在氯氣刺鼻的空氣裡。
我站在巨大玻璃帷幕牆前,像一個闖入異境的窺視者。海洋館並非日劇中的浪漫場景,一汪被精心調控至適宜「觀賞」溫度的人造海水,一片於它而言如同浴缸般狹小的蔚藍。那龐大的身軀就在這浴缸裡,沿著一成不變的軌跡,緩緩地、沉沉地,畫著永無出口的圓。它的背脊是深灰色的、沉寂的山脈,而這山脈,本應在大洋脈動中起伏。
它的記憶深處還留著怎樣的回聲?是千米深處家族間密碼般的哢噠?還是能橫跨整個海盆的吟唱?那吟唱原是求偶的情歌、遠航的號角、生命與生命在浩瀚舞臺上的交響。如今,替代它們的是廣播裡甜膩的解說、孩童尖脆的嬉笑、表演開場時震耳的流行樂。那扇曾能傾聽整個海洋的耳朵,大概早被這片人造喧囂磨得疲憊。
表演開始。訓練師跨上它的背,像一位得意的征服者。它奮力一躍,用這具身軀被賦予的全部力量,把馱著的人頂向半空,濺起巨大的、討好的水花……日復一日。看臺上傳來的掌聲,是獻給這屈從的勳章。我望向它張開的嘴——那順從的弧度像在笑,卻更像一聲被稀釋千萬倍的歎息。
「它的眼神,是我此生不敢直視的深淵。」一位前訓練員說,「那裡沒有憤怒,也沒有怨恨,只有一片遙遠、與這裡全然無關的平靜。」
我終究沒有看清那眼神。
那種平靜比任何狂暴都更令人心驚——那是放棄掙扎、把靈魂放逐到記憶盡頭之後剩下的空殼。
我們到底在觀賞什麼?
我們以為目睹了自然奇蹟,實則不過圍觀一場精心編排的權力戲法:用門票買一場幻覺——看啊,這海洋巨獸、這自由的象徵,也向我們俯首稱臣。將雄渾禁錮、將壯美馴化、將史詩簡化為馬戲,這是人類最深重的「妄自菲薄」。我們不敢在它們的主場與之相遇,便把它們拖進淺池,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滿足廉價而淺薄的同情。
那片廣袤的、真正的海在哪裡?
在那裡,鯨魚是遷徙的詩人、深潛的哲學家。它們的歌聲可傳數百公里,維繫著我們難以想像的複雜社群;每一次深潛,都是對生命極限的探問。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地球生態平衡的見證。而我們,卻把這部流動的史詩裝裱在名為「海洋館」的狹小畫框裡,沾沾自喜地指給孩子:「喏,這就是鯨魚。」
假如把水下麥克風投向真正的北大西洋,你會先聽見自己心跳,再聽見遠處雌鯨24分鐘的連續吟唱,像一座緩緩經過的藍色教堂。
那位前訓練員的告白仍在我耳邊——她看著一頭身長4米的鯨魚被圈在10米長、7米深的水池,而它本可在海裡下潛至1-200米。「7米,原來只是它一個轉身的長度……壓力和恐懼從此與它常伴。看到一個高度社會化的鯨魚在孤獨的池子中,運輸途中擠在極窄箱體,約2/3會死亡;能活下來,已算奇蹟。」
鯨魚是母系社群動物,雄鯨一生3/4時間隨母親遊弋;做為胎生動物,直到能自立才離開母親去繁育後代。因商業捕捉而來的多是幼鯨,若沒按指令完成動作,就會被剝奪食物——觀眾看到的「開心」,是饑餓下的妥協。
我轉身離開,把那片虛假的蔚藍與刺耳的歡呼拋在身後。外面陽光刺眼。仿佛聽見,那滴淚終於墜落——沒有聲響,卻比任何聲音都沉。
「沒有生命屬於牢籠,」訓練員懺悔,「沒有一個生物喜歡被囚禁。我們賭它的善良,賭贏了,再繼續剝奪它的善良。最後,它痛苦地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請不要跟著這個產業一起欺騙世界。」
真正的淚,不該為取悅誰而流。
讓它們回去吧——回到那片鹹澀、幽暗卻無比自由的深藍。那裡,才是它們該流淌、也終將歸於永恆的地方。而我們所能獻上的最高敬意,不是把它們帶到身邊,而是懷著謙卑,遠赴海洋,去聆聽、去守護那一首首屬於深藍的、真正的史詩。
延伸閱讀
- 昆蟲誌:螻蟻、飛螢、壁虎、斑蝶
- 徒步於緬甸昔卜:尋找世間美好樂園
- 人在大別山:一次山間行旅中的書寫
- 阿勒泰白樺林:大地深處編織的詩章
- 橄欖客棧:一簍青橄欖與兩張老船票
- 走進婆羅洲:諦聽自然脈搏低語回聲
- 黃綠紅三色條織毛巾 扭出的七彩歲月
- 人際生態:三位日本鄰居教會我的事
- 初夏獨戀絮語:愛著這種固執的神諭
- 靜定諦聽畫聲兩帖:夏溪圖與聽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