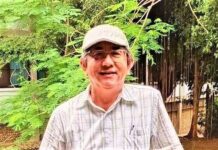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早上,詩人蘇楷過世,消息來得很突然。好比一個遙遠的熱帶氣旋,一夜間演變為強烈風暴,撼動著「朋友圈」中的萬家燈火。
如今留下的,是詩人伊夫傳給我的一卷詩稿,靜靜藏匿於電腦裏。然因與蘇楷並不相識,反讓我可以完全從文本(text)去解讀他的作品,為這位江湖上素未謀面的詩人,頌一闋禱詞、添一章華彩。
每個詩人都得面對來自八方的世相,而世相總是變易不定的,並且築構成各種形態來隱瞞真相。世道日趨繁複,不復往日的簡單,撥開雲霧已非易事,而更多的人懼怕真相,甘願一直走在霧中。
政治最能反映當下文明的滑坡,假新聞、偽事實,借法治與道德行惡,已屬平常。左搖右擺,藏鏡於後,均成正道。如此真相總是重重地被圍困著。另一方面,人類官能的局限也同樣瞞騙了自己。單以視覺為例,既無鷹隼銳利,也沒蒼蠅的複眼,更不能像蜥蝪般左右眼各自不同步的轉動。
「盲點」即我們昧於真相的最佳寫照。詩人,即是拿手中的文字,戳穿一切世相,尋找心底的真相來。那就是書寫,也是詩存在的意義。
蘇楷營造他的文字堡壘以抵抗世道。每個真正的詩人都在建構他的王國,都不隸屬於誰。〈詭異之路〉有這樣的述說:「換一種方式的遮掩,黑紗幕濃縮/我坐下,就有一個獨立的王國」。〈影像的根據地〉有:「我的孤獨在一張椅背上,依靠/誰的側面像經過翻修:陰影/超出了小墓地,從點亮燈之前」。這種「自我為王」正是詩人對當下混濁且無序的現實的覺醒,即不屈從於所有的約定俗成而自成規條,成就屬於個人的述說方式。
翻譯家梁宗岱在〈談詩〉中說,馬拉美酷似我國的姜白石。他們的詩學,同是趨難避易1。寫詩不啻是語言的冒險,往艱難處走。蘇楷的詩正是如此,拾易取難。故其詩不遷就平庸的讀者,不易於解讀。因為難解,詩人往往在題目中作出一定的提示。且看〈拋錨地〉十行,蘊藏極深:
很多東西都易逝,在錨地的縫隙中
鐵器,以幾種形式和水面接觸
從小皮筏,漂浮在年代,沒什麼
畫筆棄置一邊,因為,帆布
高於了雕塑,猶如從前喜歡的一天
很注意打魚者:直到身體在風浪
之間,好像水手們,不能
故意隱藏,殺手鐧的秘密方式
缺席的,並非影子,即使夢的
迅捷,紀念碑一樣的魚骨
詩人在雜亂的海岸旁發見了可寫之物。錨為定船器,可抵抗流逝。這裏「鐵器」一詞,對照下面的「皮筏」,成為歷史詞語。帆可御風而行,與時間爭一日之長,所以高於固體的雕塑。但這已是往日之事了,詩在這裏分前後兩部分。「打魚者」和「水手」是兩種不同的角色,也是人生兩種截然相異的境況。
類似王羲之〈蘭亭修褉詩集序〉中所言的:「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欣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詩末的收束極其精彩,連下三個驚人意象:「影子」、「夢」、「魚骨」。人生到了這階段,所有皆缺席,惟影子相伴,美夢醒了,最終只剩下一副魚骨。這詩,放在任何一冊詩歌選集裏,都是最亮眼的。
〈歷史課〉思考極深。「文字具備了穿行術,也許在頭腦/有一個流程,可是白色的塔/怎麼能克制傾斜,或者狹窄的夾角」,詩人感到語言的局限,在營造白色巨塔時,傾斜與夾角常感到難以處理。寫出來的是所期待的否,是所有詩人感到迷惑的。
這裏的「白色巨塔」,我偏向作「巴別塔」解。因為巴別塔有這樣的神話:人類建造一座通天塔,上帝便把他們的語言打亂,讓他們彼此不能溝通。這個與語言有關的塔終於停止建造2;〈夢囈的間隙裏〉也談到語言:「詞語這一隻老虎,在紙牆之上/套牙都用壞了:白色的/沒有成為一個要點」。濫用套語將連一個要點都不能表達。
再看〈對話框的擠壓〉:「……這一片/山楊樹,成就了語言中木板的欄柵/也許,很滑稽,是詩歌要押韻」。語言的欄柵即語言的邊界,山楊樹是被書寫的外物,然詩的書寫不能停留於「物」,應抵達於「物外」,否則被書寫的物,終將反過來成為語言的邊界。補救之法,可回歸於音韻。
蘇楷頗多的詩具有「後設」(Metapoetry)的意蘊,等同我國詩學中的「論詩詩」。這些詩意味著詩人具有高度的自覺(Self-consciousness),而自覺於當下混亂的詩壇中尤其重要。學者楊玉成在〈後設詩歌:唐代論詩詩與文學閱讀〉中說:「所有的詩都是潛在的後設詩歌,都在表述詩為何物。差別只是這種意識的強弱程度而已。」3蘇楷以極其顯性的自覺,朝向成熟的風格之路走去。
〈標誌著書頁上的花枝〉的「詞語的花粉,好像還有養份,其實/年代啟始了藍紫色」,〈很久離去的岸上〉的「如昨天暴風雨的箇量,被納入一個/起死回生的詞:或有一點意義/因為沒有禁錮的穹頂,等同於/白樺樹長高了許多,像另一些頭頂」。
再如〈達到用字母的訓練〉的「意象的降落傘:塗沬什麼顏色/或許,你可能牽引很多天」,〈在雪線之下〉的「靈魂喧嘩的/程度,成就了偉大的詩句」以及〈規劃了詞語的斷崖〉的「命名的東西脫落了,滑雪板,似乎/可以幫上忙:對一個線性的交戈叉點」等,都是精彩的詩論。詩人蘇楷,在創作中完成他的詩學。
蘇楷的詩極優秀,極其重視語言的煅造,在詩壇卻是一位被低估了的詩人。詩歌書寫由平庸而優秀,其聚焦點分別是:鏡外實象、鏡中影象、鏡後想象。他的詩,往往不是影像世界的重複書寫,其焦點落於不可見的鏡像之後。詩人不以目視為真實,因其內在的秩序與意義己然完成。
既有屬於個人的語言,詩的王國即宣告建立,詩人即成為流亡之君,能進入城堡的人都得通過文字的重重關隘。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 1888-1935)說:「思考會使人困擾,仿佛迎著雨行走,/風會漸漸增強,雨也仿佛更大的樣子。/我沒有野心與渴望。/成為詩人不是我的野心。/而是我獨處的方式。」詩人如今流亡天國,離開我們,成就了永恆的獨處方式。
遠離了雪柵欄:至少,冰凍的氣味
呈現在一層玻璃上,僅僅像崗哨 -- 蘇楷〈冰凍的氣味〉
(2024.11.1凌晨3時於婕樓)
註
- 姜白石曾說,難處見作者,馬拉美也有「不難的就等於零」一語。見《詩與真》,梁宗岱著,臺北: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91。
- 這個神話,見於《舊約聖經﹒創世紀》第十一章4-9節。
- 見《淡江中文學報》第十四期。
延伸閱讀
- 入座與舉手 序詩評集《低處的回聲》
- 即食,獸語:詩集《獸之語言》後記
- 厚重與單薄:詩歌中的歷史元素
- 更向詩歌高遠處:意境 語境 詩歌密碼
- 如銅錢正反:藝術家劉梅玉的畫與詩
- 從博物館到旅館:詩在篩選中
- 寂寞外傳:誰此時寂寞就永遠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