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適逢香港藝術館開展「提香與文藝複興威尼斯畫派」,烏菲茲美術館的珍藏展,第一時間去看了。
興沖沖走進去看了一陣,竟然還沒看到提香的畫,這才一時間驚覺,那是威尼斯畫派無數優秀畫家眾星捧月,一起端出的文化盛宴,提香就像百花叢中最燦爛的那一朵,除了他,可看的還不知多少。
漫步久久,終於看到提香的那些原本只能在書本上看到的原作時,才步入美術館的那份熱切與期待感也消耗許多了,只是用平常心看提香的〈花神〉〈慈悲聖母〉〈維納斯∙丘比特∙小狗與鷓鴣〉〈查理五世皇帝肖像〉(記得這幅畫在我買的《輕與重叢書》等,常赫然裝飾有關莎士比亞的書籍封面)。
提香、威尼斯畫派、法國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查理五世皇帝之間的戰爭⋯⋯大致來說,在許多人的想像世界裏,威尼斯是一個充滿了田園牧歌、優美閑適生活場景的異域,文藝復興洗禮過的熱鬧喧騰的市井生活充滿了肉欲至樂、靈性狂喜,琳琅的東西方貨物堆積如山,映射著威尼斯人繁華快樂的人生。
但平心而論,16世紀的威尼斯又是一個被人們賦予了過多文化想像的地方,就像很多人一往情深地懷念故紙堆裏的煌煌大唐,而渾然不覺,那時代的人文風貌與人的實際生活是不是差異巨大?
事實上,那年代是充滿了戰亂與痛苦的,因為威尼斯當時面對東西方兩綫的戰爭威脅,底層人民尤其活得水深火熱。而即使是王公貴族,在瘟疫、戰爭、傳染病與有殘酷傷害與殺戮的社會生活當中,貴族們的平均壽命也並不長,有專家預估絕不會超過40歲。
於是不禁想,威尼斯畫派,尤其是提香等等大畫家帶給我們的文化想像為何充滿了如此積極樂觀、快樂向上的精神呢?
那大概是由於文藝複興時代解放了人性,並使人重新意識到,自己活在這喧騰的人間,活在這上帝之靈造化、賜福的蒼穹大地。另外,也關乎藝術,因為那時候的繪畫傳統突破中世紀窠臼,確實帶給我們許多揮之不去的烏托邦幻夢。
橫空出世的威尼斯畫派當中,提香自然是最優秀的。他的畫筆下,那宛如劇場的威尼斯、如花美眷的花神充滿聖潔與肉感的胴體⋯⋯處處映射威尼斯的繁華與智性。
提香畫了無數栩栩如生的貴族肖像畫,亦徹底改變了風景畫面貌,將自然景色的塑造與人類情感緊密相連。其巨大影響轟鳴、貫通於西方油畫藝術史,直到19世紀末
印象派誕生,才算勉強越過提香大師的光輝。
然而,「弱水三千取一瓠影」,給人印象最深的倒未必就是提香的畫。如果說提香是珠穆朗瑪峰,那麼當人人都去攀登珠峰,也就讓這一攀登過程變得似有些索然無味。相反,與珠穆朗瑪峰接近的其他一些山峰,愈發使人觀之無厭、歎為觀止的。
譬如印象挺深的是許多充滿了嚴格寓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畫作,如巴里斯·博爾多內的〈騎士肖像〉,畫中的年輕人將右手放在一張覆蓋白布的桌子上,桌上擺放著一個花冠和一頂頭盔,頭盔頂部的維納斯手持花環(象徵著婚姻),桌子旁則有一支與頭盔相配的長矛。
貴族年輕人穿著紅緞衫、紅短褲、黑夾克外套配披風,一腿略抬,顯出緊身褲綳緊的好身材,而他目光斜睨處的一角是一幅畫中畫,畫的是一位年輕女子站在一座威尼斯大型建築內,正接收邱比特的信件。可以設想,這幅畫描繪的是訂婚場景,戀人對其心愛之人表白並展示力量,畫面將這一切相得益彰地隱晦表達。
巴裏斯·博爾多內是提香的學生,並承繼了他對溫暖、深沉色調的喜好,這幅畫讓筆者久久駐足,驚嘆於它精準的寓意和畫工的精湛。
展場外也有香港藝術家爲這次展覽特別製作的致敬藝術裝置與畫作,威尼斯玻璃燈具當中折射著幻變的光彩,再配上藝術家特意到威尼斯搜集的海潮聲、十多幅水墨畫。使人感嘆:威尼斯人在如斯的繁華與傷痛的歷史進程中,為我們留下了神性與人性共同凝聚於當下現實生活的藝術,至為樂觀、積極向上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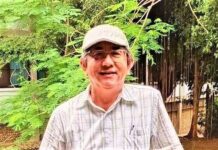










言簡意賅, 真不容易, 可讀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