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看畫家盧巨川的鋼筆畫《香港舊郵局》不禁興起懷舊之思。這幅畫寫於一九六三年,把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一幢舊建築物的形貌保留下來。鋼筆畫值得欣賞的地方,是那些奇妙的藝術線條。這些線條,是畫家的「心象圖」。譬如畫家看到建築物外牆的彎曲,那「彎曲」便即真實,我們不能以科學或理性的思維來分析,說哪有一座大樓的外牆如此扭曲,那不就成危樓了嗎?
名家以線條來勾勒事物的輪廓,區分深淺、粗幼、疏密、直橫、斜曲的不同,便能組合成一幅「寫實」的傑作來。此畫的主體郵政局,為一舊式建築物,保留了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風格,其存在的壽命為1911-1976年。位於畢打街,即今日中區環球大廈的基址。
《百年前的香港郵政》一文,寫道:「後來,中環填海,竹棚郵局已失地利,而且郵政業務日趨發展,原址不敷應用。一九一一年,在畢打街海邊,建昔樓高數層的新郵政總局。」然時間巨輪從不停歇,昔日的「新」已成為今日的「舊」。而今日的新郵政總局,建在舊稱康樂大廈的怡和大廈前臨海處。

畫中那幢舊郵政總局,服務香港達七十年。其大堂內一道牆壁上的實木拱牌,移至今日郵政總局的一樓大堂掛放。行人路客,常歇腳指點,喚回記憶。歲月留彩,這種「新」與「舊」的交替,便成了都市發展的痕跡或傷疤。
這幢舊郵政總局,當然有著一段光輝歲月,也曾經是一幢「現代化」的建築物。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鄰近的高樓大廈愈蓋愈多,才顯露出它的「寒傖相」,最終難逃拆卸的命運。
我記憶中的舊郵政總局的那個年代,港島街道上,仍行駛著有車頭的舊式雙層巴士。年輕人仍穿著關刀領的裇衫、喇叭腳的西衭,披著一把長頭髮,留起鬢腳來趕時髦。那是披頭四(The Beatles)文化泛濫的時代。
那時,我是個中學畢業生,正為前途傍偟。因為貧窮沒錢報考香港大學的考試。後來到了台灣,命運由之變改。那時,許冠傑的俚歌在通衢小巷中響起;臺北巷弄間卻泛溢流行著鄧麗君的抒情小調,……畫中那棟郵政總局的前方,是卜公碼頭。由郵政而交通,倒使我念及更遠以前,屬於童年時代的一些往事來。
六十年代,我在何文田黑布街一間基督教小學唸書。那時,父親是個貧窮的教書先生,收入有限,家中生活捉襟見肘。父親極嗜舊詩寫作,常在《華僑日報﹒文化版》用粲花先生、餐霞道人或六安居士的字號,發表舊詩,作品包括當時頗有難度的集句和回文詩,因而頗具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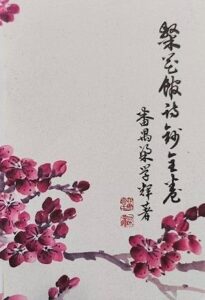
許多時候,父親會在傍晚時分,拖著哥哥和我,往佐敦道碼頭乘小輪渡海到中環,然後徒步到砵典乍街的華僑日報辦事處交稿。那時,郵遞沒有現在的便捷,為趕時間,父親常託人帶稿或親身交往報館。那時,父親的身體還很壯實。寫在白信封上的字仍是剛勁有力:
煩交 華僑日報 雷浪六先生 收
後來,吳灞陸先生任旅遊版編輯時,父親仍在寫他的旅遊詩篇。一直到他逝世前兩年,身體衰頽,握筆乏力,才迫不得已停筆。然這些詩句卻常在我心裏:如〈 暮春集鯉魚門懷花館主冼茗總 〉:
去歲歸來汗漫遊。揚帆又別客南州。風搖古樹疑天動,山入澄江共水流。
烽火危時同避地,夕陽深處莫登樓。懷君況值鶯花老,極目徒牽萬里愁!
再如〈 次韻逸翁招飲瓊華樓 〉:
百年將半莫籌謀,物慮空移夜壑舟。亂世無人安壟畝,詩壇猶得共茶甌。
獨憐性梗難隨俗,漸覺才疏不入流。細雨黃梅招我醉,筳前覓句勝封侯。
如今,新郵政總局、新卜公碼頭,新的中區已然建成,地鐵的中環站和香港站匯合於此。但舊事如舊畫,在我的憶念中,時刻常新。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