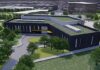去土地廟拜神,廟有點小,土地遼闊,神仙遼闊,心跟著一起遼闊。
遠處的雪山,頭頂的暖陽,曬太陽的火梗犬。這些,足夠一曲長調。
寫首小令吧,擠進文化週末(一檔報刊的欄目)的縫隙。這樣好,不會拋錨的自由小空間。
倘若被擠成水腫,那是小令沒能接住春天的權杖。
春光照耀字母A,同樣光顧字母Z。
倘使遇到白紙無字,打開窗戶吧,銀蛇爬進來,吉祥吐出新蕊,枇杷花就開了。甚至,某個枝條,極小極小的果實攢在一起密謀一場冒險:
爆竹聲聲,年躲進了鐵籠子。
香火點燃,春天和大地結婚——
河水嘩嘩,柳絲唰唰,草仙子吧嗒吧嗒。
料峭的日子只剩下兩顆智齒,咬不動春光滿面。
迎春花像一枚枚鵝黃色耳扣,鑲嵌在春姑娘長髮虛掩的耳垂之上。
桃花,盡情地綻放。春風不笑她,她不笑春風。
郎在對面唱山歌,頭頂陶缽的少女,赤腳走在田壟上,回眸的一瞬,千萬畝梯田敞亮起來。
麥苗返青,桑煙升起。陽光灑進屋子,君子蘭、幸福花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盆栽抖落滿身的疲憊,吐出新綠。
布穀,布穀——
這是鳥類語言,也是大自然的鈴聲。
在春天的基因序列裡,天地相認,動植物生死與共。雨水配好血型, 琥珀色的黎明滴進漿果色的鳥鳴中。
該先叫醒誰呢?三分春色,兩分塵土,一分流水。
魚兒游上了岸,鳥兒拎著福字倒著走。
說到流水,繞公社回到杏花村。蜂蝶自在舞,嬌鶯恰恰啼。
我所渴盼的二月蘭,翹起了蘭花指。
母乳餵養長大的山嶺免疫力增強,脫掉最後一層外衣露出深深的鎖骨。畫眉落枝頭,淺笑無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