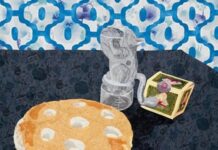01
澳門的黃昏與別的城市不同。來澳門前,我會在黃昏情不自禁地放空大腦,無止境的憂鬱讓我對黃昏心存恐懼,我極力避開在黃昏出門;但澳門的黃昏相反,它讓我感受到生命的絢麗多彩。
晴天,澳門的黃昏溫暖而又豪壯。仰觀藍天,眼睛、心靈變得澄澈;面朝大海,人的心胸變得寬廣起來。遠遠望去,海面靜得出奇。岸邊,榕樹須是小島的裙擺,在慢悠悠地飄拂。偶爾有黑臉琵鷺飛過,像一條雪白項煉,也像珍珠髮卡,點綴於小島。
半空中的橘色晚霞在燃燒,陸地上的火紅鳳凰花在搖曳,微風變成一面明鏡,讓它們相互映照。太陽西斜,婆娑倩影倒映在水中,像一隻橙子,從樹葉中探出頭來;也像一枚故鄉的蛋黃,正在被沸水翻滾著煮熟。
路環碼頭有人垂釣,魚或螃蟹被裝進水桶。魚上鈎,一群游客上前圍觀。說粵語的老伯熱情地給我們介紹魚的種類,哪一種魚該怎麽烹飪。「我今天拿到的這只螃蟹很好看的,你們要拍照嗎?拍照不收費的。」知道有人聽不懂粵語,老伯改為普通話說著,隨即徒手從水桶裏拿出螃蟹,空出來的另一隻手比了一個「耶」,讓我們拍照,沒有任何一點不耐煩。
很久以後的一個黃昏,當我再次去到路環碼頭,雖然沒能再見到那位老伯,但他此前的真誠笑容仍然映在我腦海中,於是陰天也變成了晴天。
02
春節期間的澳門,據說媽閣廟最熱鬧。大年初一這天,我和小友鹿鳴約好去媽閣廟走一走。黃昏來臨前,我們成為那一天最後進入媽閣廟的兩人。
順著石階一路往上,烟霧繚繞,最高處有一小片竹林。我們坐在不規則的大石頭上,靜靜地看夕陽穿過竹葉、竹枝,像一串孤零零的橘子糖葫蘆,緩緩沉入大海。媽閣廟的管理人員看我們身穿漢服,特意前來與我們交流儒釋道文化,然後一同下山。他拿一把長掃帚,在橘色暖光下清掃著人們來過的痕跡,包括我和鹿鳴的。天黑了。
我和鹿鳴沿著河邊新街走,試圖找到當天的晚餐。空蕩蕩的馬路上,除了偶爾路過的車輛,只有我和鹿鳴兩人。路旁有一排餐飲店,却只有一家餐廳開著門,餐廳的員工正在圍桌吃晚飯,很熱鬧。
我們不得不繼續往前走,想要找到最近的巴士站。途中路過一座福德祠,還開著門,看護的阿姨面帶笑容問我們是哪裏人,是不是因為疫情才沒回家過年,然後從屋裏拿出兩個紅彤彤的大蘋果,送給我倆,祝福我倆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媽祖信仰和土地信仰都屬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産。福德祠在澳門俗稱土地廟,顧名思義,土地廟供奉的是土地公,又稱為「福德正神」。在澳門,土地信仰傳承已久,河邊新街的福德祠建造於1868年,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三十二平方公里的澳門,供奉的土地廟近十所,公共土地神壇多達一百四十個。此外在澳門的屋苑住宅、商鋪大厦門前隨處可見土地神位。
03
從氹仔島去澳門半島通常會經過一座長約2.5公里的跨海大橋——嘉樂庇總督大橋,又被稱為「澳門鏡海長虹」。
橋如其名,嘉樂庇總督大橋如一道銀虹,架於海面,本身就是道令人驚嘆的美景。晴天的黃昏路過嘉樂庇總督大橋,放眼望去如同一幅幅蔚為壯觀的油畫。大橋一側的海域正在逐漸縮小:貨船拉來泥土,將海水填平。
遊輪駛過,渾水現身,一道又一道土黃色的細綫被拉長,擴散開來。一隻白鷺低飛,銜著黃綫飛向海天相接處,綉出漫天火燒雲。旅遊塔斜上方,火燒雲像絲綢織成的翅膀,四周點綴橘紅色的、藍紫色的、水粉色的淺淺雲霧,像一襲溫婉的粉黛亂子草。
無數次乘坐巴士經過嘉樂庇總督大橋的黃昏,我開始意識到人性的貪婪。我們想要用相機定格窗外美好的瞬間:譬如一隻黑臉琵鷺安詳地站在一根欄杆上,人們花了不少時間去辨別它是真鳥還是雕像;夕陽在海平面上空顯得異常奪目,我們能清晰地看見並且感受到它在平緩地下滑。
我們篤定站得越高,看得越遠。所以,為拍到最大最圓最紅的夕陽,我們雙頭抬著拍照設備,就等巴士到達跨海大橋最高點時,立即按下快門。然而,很多時候,當我們真正到達嘉樂庇總督大橋的最高點時,夕陽早已回到山的背面了,相機能拍到的西望洋山以及西望洋聖堂也已經籠罩一片灰暗。
想拍到最好的夕陽,我們最終却連夕陽的影子都拍不到。後來,我們學會珍惜眼前,不再刻意追求完滿。因為我們在嘉樂庇總督大橋走過的每一步都不是重複的,每一時刻的夕陽,也自有其獨一無二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