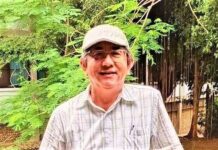詩歌是一場烈火,而不是修辭練習。--海子
唸大學時代,關於新詩的「熱門」評論集是陳芳明的《鏡子和影子》[1]。書的首篇是常為人們引用的「詩無新舊,只有好壞」。那個時代的臺灣新詩,標榜反傳統的「橫的移植」,稱新詩為「現代」詩,陳芳明無疑是臺灣新文學與傳統割斷後的一次醒覺。
在談及李金髮等詩人的「象徵主義詩歌」時,詩人廢名在〈談新詩〉一文中曾明確指出,現代派是溫庭筠、李商隱一派的發展,在文章最末,他說,新詩的前景很光明了,因為舊詩的長處可以在新詩裏得到發展[2]。可見傳統詩歌對新詩的影響,一直是優秀詩人的自覺。那些盲目崇洋,排斥傳統的詩作者,浮沉在詩歌的汪洋大岸中,一直不能抵達彼岸。
傳統詩歌的影響對每個以漢語創作的詩人來說,一直存在著。因為漢語本身便蘊含著牢不可破的傳統文化。儘管我們現在的白話詩形式上模仿西洋,藝術審美準則也遵循西洋的尺度,但在優秀的白話詩裏,我們始終看到其精神內蘊對傳統文化的承傳。
一九八九年,以二十五歲之齡臥軌自殺的詩人海子在〈我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中說:「必須克服詩歌的世紀病,──對於表象和修辭的熱愛,必須克服詩歌中對於修辭的追求,對於視覺和官能感覺的刺激,對於細節的瑣碎的描繪。……詩歌是一場烈火,而不是修辭練習。」[3]確然,現在許多的詩歌仍耽溺於西方修辭的追逐,而忽略了詩歌傳統人文精神的承傳。
那種「競技般」的作品,眩目惑心,並因之難以解讀,背離了我國詩歌源遠流長的傳統。海子一往無悔的傾心於荷蘭現代派畫家梵谷,但海子詩歌的精神卻是中國的。如果說海子的詩歌有難解處,即這種難解並不是因為修辭故,而是因為詩意故。
梵谷的畫作不乏以「麥地」為題材的作品,如「有柏樹的小麥地」、「麥地上的烏鴉」等,「麥地」在海子的詩歌裏同樣不罕見,如「麥地」、「五月的麥地」等。試看「五月的麥地」[4]的末節:
有時我孤獨一人坐下
在五月的麥地 夢想眾兄弟
看到家鄉的卵石滾滿了河灘
黃昏常存弧形的天空
讓大地上滿佈哀傷的村莊
有時我孤獨一人坐在麥地為眾兄弟背誦中國詩歌
沒有了眼睛也沒有了嘴唇
說這首詩其精神內蘊是中國的,不在於詩句裏出現了諸如「家鄉」、「村莊」等傳統詩歌的「詞彙」,也不在於詩人提及了「中國詩歌」這一強化的標籤,而在於詩句背後那種文化(人文)脈絡。詩人趟在安徽的麥地上,想及的是因為貧困而四出謀生的眾兄弟,想及的是因為貧困而滿佈哀傷的村莊,詩末「沒有了眼睛也沒有了嘴唇」,隱隱然有「無我」(「與萬化冥合」)與「忘言」(「欲辯已忘言」)的意境。
我學習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傳統文學影響我的新詩創作,自不待言。那種影響有時是「顯性」的,但更多時是連我自己也不察覺的「隱性」的存在。最近我遇上了寫作的一個罕有「經驗」,傳統詩歌與我接軌,竟是如此直截相連。
某個深宵,我讀杜甫五律〈獨坐〉,忽爾感受百般湧現,自覺當下頗能夠感悟到詩人的處境,便也寫起了一首〈獨坐〉來,也是八句,當然不用韻不合律,完全是自由體的白話詩,但其情況卻有點像舊體詩的「和作」。杜甫的〈獨坐〉[5]是這樣的:
競日雨冥冥(1),雙崖洗更清(2)。水花寒落岸(3),山鳥暮過庭(4)。
暖老思燕玉(5),充飢憶楚萍(6)。胡笳在樓上(7),哀怨不堪聞(8)。
這首五律是杜甫晚年的作品 ,除了詩的「頸聯」較受爭議外,其餘皆可解。詩人暮年,既寒且饑,但個人的窮困不足以言哀淒,「思」與「憶」自可排遣。值得哀怨的,是那意味著戰火連連的「胡笳聲」。八世紀的大唐皇朝與二十一世紀的特區香港,人文景觀、社會面貎,自不可同日而語,其相通者惟人心人情之靈犀一點。我的〈獨坐〉按杜詩每句對應著來創作的,如後:
(1) 回暖的季節給天空抺上一層灰黯的心事
(2) 兩岸的高樓大廈透露著這個城市的虛浮
(3) 亂了時序與方向的候鳥枯立在簷頂
(4) 月亮及早升起,那時夜晚仍未降臨
(5) 疲倦令人聯想到那些香薰油的味道
(6) 飽食後便憶念起那片非常的黝黑
(7) 推開窗門時傳來動土的機械聲
(8) 是那樣的叫囂著要把記憶變改過來
論宏大開闊,意蘊深沉,我的當然不及子美,去殿堂遠矣!但這首詩是「忠誠」於我當下的感覺,並效法了杜甫,由個人的感覺推放到時代社會裏去。那時我的情緒低沉,獨坐陽臺看著這個充滿著虛浮的城市,大環境(自然)在城市的荒誕裏也混亂失序。
「疲倦」和「飽食」是城市人的兩種顯著的病徵,無論我們是如何的運用「集體」的力量,科技的霸權照樣干預著我們的「記憶」,生命變得這樣真令人很無奈和傷感。我寫作的那刻,感覺和杜甫的「獨坐」相通,我借助了傳統詩歌的力量來創作。
只是想說明一個問題,無論形式和內容,在大傳統底下,新舊詩歌的承傳關係,雖則曾因外力而出現斷層的現象,曾經走遠了,但傳統卻一直以潛在的方式影響詩人的創作,傳統的力量終必令詩歌回歸文化本位。
海子說,詩歌是一場烈火,而不是修辭練習。我補充,詩歌是一場傳統的烈火,而不是西洋的修辭練習。這場烈火,燃燒著傳統的乾柴,方能顯示他的力量。
註解
[1] 《鏡子和影子》,陳芳明著,臺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
[2] 〈談新詩〉,廢名著。本處轉引自《現代派詩選》,藍棣之編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
[3] 引自《解讀海子》,高波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67。
[4] 《海子的詩》,西川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頁101-102。
[5] 《唐詩答疑錄》,張天健著,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頁113-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