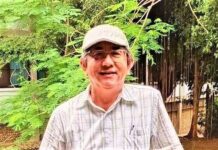八月高雄城,風雨過後。一個天陰午間,到了新興區錦田路的「逍遙園」悠轉,一座日治時期日本大官的住宅。在玻璃櫃的一卷日文古籍裏,看到「日治時期台灣十二勝」的記載,其中有「虎頭埤」之名。同時列名的還有桃園的「大溪」與「角板山」。回去後網上搜尋,竟誤把臺南新化區的「虎頭埤」誤作桃園「虎頭山」。乃有虎頭山之旅。
久未再訪桃園,往事在縹緲中,頗有「前度劉郎今又來」的蠢蠢欲作之思。乘早上九時半的高鐵,到桃園站已是十一時。會合友人後,便先在領達廣場的「果然匯」午餐。吃主餐時,窗外日照明朗,火車站附近雜亂的房子擁擠在一起,頗有煙火桃園之人間美。
到品嚐甜品與咖啡時,天色轉陰,稀疏的雨點飄浮於空間。風起而雨不大,那正宜登山。由是想及行程前翻看的黃曆,列明「閏六月廿八宜出行會友」,冥冥中果然有定數。虎頭山是桃園市區勝景,計程車直接把我們送到山上的「環保公園」。也開啟了虎頭山之旅。
此時雨點變密,但仍可不打傘而行。這兒是一個地臺,雖不挺拔崇高,卻也足以俯瞰桃園市全貌。高處眺望一個城市時,我總會想到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他的許多作品裏,都有過類似這樣的描寫。做為現在的書寫者,不能避免地起居生活於「我城」,然久處安樂讓人心靈遲鈍,成了書寫的無形障礙。

置身事物當中時,我們成了「事物鏈」的構成部分,而當我們排除於事物之外,那時便更能看清楚:相對局部的是全部,相對利害的是清白。如此,思想便自然出現了另一種「審判」來。由是得詩如後:
我的保護色 / 秀實
—自虎頭山俯瞰桃園市
那些不同的建築物
都有它們的名字或號碼
拐角處的某個車站
某間餐桌上的半杯熱咖啡
以及,一場給我命名了的
雨。此時仍在下著
曾經的場合在進行中
有些顏色是想保護的
稱為我的保護色
此時,整個城市都是
另一種色彩,曾經的人
帶著他的顏色離去
城市的顏色並非我們所見的,而是由「這一切」的人來替你決定。譬如此時自虎頭山上看桃園的天空,灰壓壓一片。右側濃厚的烏雲中央處墜下,那是新竹市的方向,正下著一場瓢潑大雨。我們會說,黯淡的灰。而其實這是假象。
實際的色彩並不如此。你心裏的「這一切」的人會替你塗抹上別的色彩,或帶走了某種色彩。而在歲月沉澱後,那才是真實的顏色。這種論述,恐怕極其少數的詩人才了悟於心。
很常見的南方佳木「榕樹」在山上等待我的來臨和告別。它們會說,「來了啊」與「要走啦」,此時我會沉默地從樹下穿過,踩著落葉與心事,讓時光放慢腳步。「急」與「閒」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而所謂優秀的存在,其真實意涵是「詩歌式」的,即只可感而不可解。所以,所有身外的人與事,為「一切」,並不具有任何參考值。

經驗告知我,人必常時讓自己處身於一個物理性的高地,思想方能脫離世俗的糾纏,返抵初心與本真。古人常有登臨賦詩,即便是生命的一次淨化。東晉王粲「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如是。近代詩人毛潤之「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也如是。
九江合流於長江,而京廣鐵道為城市的標誌橫跨江上,城市賁突,讓我們看不到一切壯麗均源於自然。登高攬勝,才幡然悔悟。如這次登虎頭山,思想上的感覺便特別美好。
山頂平臺上有三座「涼亭」,造型不同,各據一方,然均居高臨下,看大地陰暗漂移,看天空晴雨變異。山上的日照與城裏的月光是兩個不同的世界,猶如一座城市的夜間與白日,同一空間而恍如異域。
我們選擇徒步下山,讓心裏的想法,「咀嚼」成營養。回程的高鐵速度裏,我想,今夜窗前,或會有月色蒼涼,「轉朱閣,低綺戶」。城市稠聚了所有的人,網絡覆蓋到每個角落,然每一個人都是孤寂的存在。(2025.8.24零時35分水丯尚)
延伸閱讀
- 訪張曉風舊居:兼憶遙遠的大學日子
- 澄清湖:詩卷中不滅的湖光與念想
- 現實的糖城和文字的挪威森林
- 燈火長沙橘子洲:真實亭閣虛構的宅
- 秀實居:雨來便敲響寫作時的鍵盤聲
- 成都寛窄巷子:走讀一本活圖書
- 贛遊觀止:滕王閣 石鐘山 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