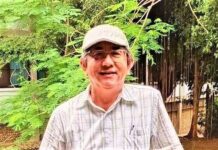在嘉義的故宮南院鄰近高鐵站,十分方便,有專車往來其間。南院設計以線條與形狀為主不務色澤。網上有人譏之為「棺槨」,而這正中設計者下懷。故宮所藏者,出土文物為大宗,並皆多從古代帝王將相的墓中發掘出來。遊客仿如走進一個「大棺槨」中,溜覽古物。
這與臺北故宮的紅磚綠瓦、雕梁畫棟的宮殿式,大異其趣而各有千秋。或曰,這殊不吉利耶。則知現代人較之古人更迷信。古人有把棺材先放家裏的做法。以其諧音「升官發財」吉利,有僻邪避災效用,並能對後事作未雨綢繆的妥善安排。嘉義小城,既有阿里山庇護,復藏納大量先人文物福蔭,必能成就其上吉風水地運。
我曾多番造訪南院,目睹的國寶不計其數。每次參觀這些具有悠久歳月痕跡的出土文物,都帶來內心最深處的顫抖,好比一次板塊運動所造成的深層地震般,自衛星俯瞰,若絲毫無損,然災區樹倒屋塌,滿目瘡痍,令人驚悚。
由是我總想及波蘭詩人辛波斯卡(Wisława Szymborska, 1923-2012)〈博物館〉中的名句:「王冠的壽命比頭長/手輸給了手套/右腳的鞋打敗了腳」。人生如寄,何其唏噓。但文物是時間留下的廢墟,我們隔著玻璃窗看,今日南院四週風光如畫,也終必成為後人所觀看的廢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這是鐵律,永不變易。
正如另一首新詩〈在博物館〉:「有人走到一個陶罐前/俯瞰古樸的花紋/有人圍著一隻青銅鼎,讀出上面的銘文//也有人,在銹跡斑斑的弓弩旁/著迷於射獵的場面/而我//獨自走向一面銅鏡/我總是不放過/任何一次看清自己的機會」。遊人只驚嘆於文物的精雕細琢,而漠然於「物」「我」間的關係,須知人常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物之奴,而非物之主。「身外物」知易行難。
最近的南院遊,是觀賞一個叫「江戶浮世之美」的展覽。日本江戶時代,即公元1603-1868年,約二百五十餘年,相當於明末至清中葉時期,是日本最後封建皇朝幕府時代。
浮世繪的藝術創作,因社會的承平富裕而興起,是日本獨有國民藝術,品目繁多,最為人談論的是其「春宮畫」。好比捲起珠簾,讓房間內的閨房樂展現於世人眼前。其他如風景畫、風物畫、花鳥畫等等,均不乏精彩之作。
我以為欣賞這些時代性強的藝術作品,必得對那個時代有所了解,方才讀懂畫意。如鈴木春信(1725-1770)的〈雪中相合傘〉(1767年作),畫的是情侶共撐一傘在雪中漫步的情景。男的穿黑,女的披白,極其浪漫溫暖,陰陽調和,意境幽邈。然實情是,當時的日本不可能男女共撐一傘,畫中男女只是嫖客與妓女的關係。
這次展出有葛飾北齋的〈富嶽三十六景:神奈川沖浪裏〉原稿。畫中展現了巨浪與富士山的動靜之美,技法創新並用柏林藍染料,為浮世繪代表作。此畫銷售最佳,印刷了約八千張,然留傳到今的不足十張,被各大博物館收藏,成了鎮店物。畫中浪尖如獸之利爪,極其駭人,也表達了大自然的威力。一群猛獸正蹂躪著富士神山,一場神魔間的爭鬥正在進行中。
另一幅是梵谷(曾臨摹過此畫)和我都喜歡的歌川廣重(1797-1858)的〈名所江戶百景:大橋安宅驟雨〉(1857年作)。突如其來的驟雨讓橋上的行人措手不及,加上斜向的橋身與雨線,使硬的線條成就了畫面的動感。畫中場景是東京「新大橋」,對岸「安宅區」因停泊了幕府軍艦安宅丸而得名。人生如過橋,並會遇上風雲驟變的時刻,橋讓人渡而不涉水,帶來安逸,然總不能忘記居安思危。
佚名的〈東海道五十三次〉也極其精彩,有若〈清明上河圖〉,全面集中展現東海道,今東京至京都一帶的風俗民情。畫家沿途作畫,這裏的「點」,是停留處,即畫家停在此處作畫之意。如〈日本橋〉、〈江尻〉、〈蒲原〉、〈原宿〉、〈沼津〉等,獨賞各呈小品異彩,合觀即無異於長卷磅礡。展出的浮世繪有二百幅之譜,如細賞慢讀,可勾留一天。
遊南院,極愜意,對思想也常帶來如激光般的一點沖擊,點中人生的盲點、病點,藝物雖身外事,然具教化之無言效用。(2025.6.30中午12時高鐵漳州往深圳1卡2F座。)
延伸閱讀
- 贛遊觀止:滕王閣 石鐘山 廬山
- 澄清湖:詩卷中不滅的湖光與念想
- 杜甫草堂:過成都朝聖大雅李杜諸堂
- 鳥圖說:我與十二種鳥的版圖(上)
- 鳥圖說:我與十二種鳥的版圖(下)
- 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哪個才是真相?
- 港事舊畫憶念常新:舊郵局與粲花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