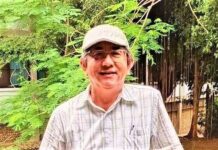海娜花的紋路,總是向外舒展,又在不經意間迴旋收攏,它的紅褐色藤蔓繞過手腕,像一種護佑,也像一份低聲的誓約。那一刻,我坐在婆羅洲文化村的竹椅上,任攤主將染料輕描在我的手背。
為我畫花的是一位男士,膚色被陽光烙成古銅,手背佈滿細密的老繭。他的手很穩,像熟悉土地的人在播種。他告訴我這染料取自樹葉,植物汁液浸入皮膚,幾日後顏色會淡去,但它的根系依舊深埋在泥土裡。
這句話讓我怔了片刻。婆羅洲的文化,何嘗不是如此?生命向陽而生,卻永遠依附著大地。海娜在我皮膚上留下印記,植物與肌膚的短暫聯姻,成了自然與人類一次溫柔的握手,它也提醒我:所有文化的根,都藏在看不見的深處,等待有心人去觸摸。
婆羅洲文化村入口,是張擺滿故事的餐桌,咖啡在木杯中沉默發黑,濃得像夜晚的熱帶雨林;蜂蜜的金黃,則是雨林縫隙中忽然墜下的一道光;米酒與釀酒的香氣,像時間的低吟且穿過空氣,攜著古老酵母的氣息。
鐵板上,印度飛餅在空氣中反復翻轉,像一片試圖逃離塵世的葉子,卻最終回到火的懷抱;旁邊的咖喱雞泛著油光,是土地、香料與火焰的合謀。婆羅洲的飲食沒有矯飾,卻在口舌之間,講述了一個島嶼與海洋、雨林相互饋贈的故事——它們的關係,不是供需,而是依存。
沿著濕潤的小徑,我們走向巴瑤族的高腳屋。那是一種生長在海上的建築,木柱筆直插入海底,像海浪下的根,木材經風洗禮,顏色褪成灰白,觸手卻有生命的溫度,樓梯狹窄,每一次吱呀都是歷史的回聲,屋內空曠,海風穿牆而過,帶來鹽與海藻的味道——漂泊的民族,在潮汐之間,給自己搭建了流動的家園。
毛律族的戰屋與巴瑤族截然不同,收斂了海的溫柔。它蹲伏在土地上,屋簷壓得極低,四周削尖的木樁像一圈冷峻的利齒,屋內光線略微幽暗,戰鬥的盾牌掛在牆上,裂開的木紋似乎還留著戰火與衝突的餘溫。
這裡的建築告訴我:生存並非安逸的禮物,而是向自然與敵手同時交出的答卷。卡達山-杜順族的長屋,像一條橫臥的大地之獸,屋頂以棕葉層層疊蓋,厚密如鱗片,既擋住熱帶驟雨,也隔絕烈日炙烤的鋒芒。
牆壁與地板由竹木編織而成,竹節之間留出的細縫,讓風自由穿行,帶走濕氣與悶熱。屋內竹席分隔著空間,既保留了私密,又維繫了共聚。藤墊發出的“沙沙”聲,仿佛土地在傾聽人的心跳——在這裡,房屋不僅是庇護所,更是人與土地之間的契約。
正午的空地上鼓聲響起,舞者們開始了他們的敘事。腳步模擬插秧與播種,身形勾勒獵行的瞬間,竹竿擊地的節奏像大地在應和。婆羅洲的舞蹈,不是表演,而是一部活著的史書。
舞畢,技藝登場。老人鑽木取火,摩擦聲與飛散的木屑間,火星如神話中的初生之光。年輕人蹦高摘取果實,似森林裡的精靈;竹制吹管在手,目光凝定,祖先的獵影仿佛在背後重現。木橋在腳下輕輕搖晃,溪水穿過石縫,發出不屈的低語——這是自然的脈搏,也是文化的回聲。
當我回到村口時,手背上的海娜花已在陽光下沉成深褐,它是植物的印記,也是文化的花紋。我忽然意識到,這裡的一切——食物、房子、舞蹈、技藝——都在重複一個主題:自然與文化從不是平行的兩條線,而是彼此纏繞、生死與共的藤蔓。
皮膚是記憶的延伸。海娜終會褪色,但它的根始終在泥土裡,就像婆羅洲的人們,始終與雨林、海洋、風,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