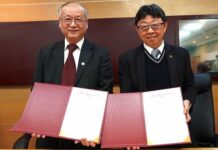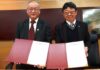薩克斯教授在《永續發展新紀元》一書提到,高等教育在「內生型成長」與「追趕型成長」的國家中,扮演關鍵角色。就我的觀點,經濟發展是以投資為基礎,教育所累積的「人力資本」代表個人與整體社會,在工作技能與生產力的提升,更是推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力量。
所謂「內生型成長」是以科技突破為基礎的經濟成長。通常由擁有高學位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密集研究發展所產生的結果。研究發展不以大學單一機構為基礎,而是靠多所大學、國家實驗室與高科技企業的網絡建構而成,這也就是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打造出來的「國家創新系統」。
至於「追趕型成長」是指採用來自外國的科技。此時,大學的角色是培育適當的人才,做好使用這些新科技的準備。不過,有些科技無法直接移植或撿現成的,必須經過調整以適應本土需求。這時,大學培育的專業人才就很重要。從早期的農業技術、紡織與民生工業、石化鋼鐵等重工業、資通訊與半導體產業,到最近離岸風電等綠能產業,都是藉由引進國外技術與人才發展起來的。
台灣戰後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使得我們已從過去純「追趕型成長」,逐步邁入「內生型成長」的階段,這期間高等教育扮演重要角色。尤其,面對當前科技時代,更需要大量擁有碩博士學位的專業人才投入研發與產業創新。國內各大型集團企業應與大學密切合作,不僅只提供產學合作機會,還可建立企業內訓管道,鼓勵員工在職進修與提高生產力。
大學同時還有責任要協助所在社區,找出並解決永續發展的本土問題,像是面對貧窮、疾病、氣候變遷、新科技等,就近協助量身打造在地解決方案。這些問題通常都很複雜,甚至遠超過地方政府機構的能力,需要各關鍵大學跨校合作解決。台灣高教目前在這方面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舉凡生態保育、公共衛生、災害防治或社區營造,都能看到不同大學師生共同努力的身影。
美國長期倡導由各大學協助解決這類國家發展上面臨的問題,特別是對聯邦政府在各州支持與資助的大學,要求的不只培育人才,還要跟所在社區合作解決當地問題。我認為這正是當初台灣鼓勵各縣市廣設大學的主要目標與初衷。
只可惜政府後來放任各大學自主發展,多數新設的公私立大學終因缺乏整體規劃,使得資源往頂大集中,少子化影響逐年加大後,各校為求生存只能顧著搶學生,顧不了原先一縣市一大學的辦學宗旨,也削弱大學在地功能的發揮。
以目前正往綠能大力發展的彰化縣來說,包括: 離岸風電、電池與電動巴士等重大投資正積極推動著,按理說這時大學培育與產學合作可以起相當大的貢獻,然而實情是,在南彰化長期投入農業、綠能、觀光等領域,成效有目共睹的明道大學,今年已被教育部勒令停止招生。不只是大學,高職也有相同的遭遇:台東縣的公東高工,一直是培育原住民木工等技職人才的搖籃,今年也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同樣在未來可能面臨停招的命運。
大學受少子化影響招生嚴重不足,這是顯而易見的威脅;學生普遍學習意願低落,可能才是經常被忽略隱而未見的重大問題。我認為這源於中學教育階段,許多學校的教學與考試,對所謂標準答案的重視遠多過思考過程的傳授,課堂活動要求學生聽話更甚於鼓勵個人觀點的表達。
社會長期對學歷存在迷思,相信文憑甚於專業,也因為這樣讓學生在長期的壓抑與挫折中,失去對學習的熱情、缺乏探索自己的機會。從國小到大學,甚至畢業後考研究所或應聘公職,幾以考試取材為主,難怪聯考取消後,補習班非但沒有消失,反而更朝專業分科上設立,在台灣各式各樣為考試而設的補習班林立,甚至有所謂補教利益共同體的畸形發展。
台灣的高等教育在這個科技高速成長時代,所要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面臨的挑戰更不少。就像人類社會在追求永續發展的過程,需要解決的問題都非常複雜,在在考驗每個人的智慧。然而我相信,教育部若能借鑑美國聯邦政府補助地方大學的作法,共同打造台灣「國家創新系統」可能是化危機為轉機的策略思考核心。
當我們暫且從少子化與政治考量的綑綁中掙脫,在喘息時不妨回到一縣一大學的思考基礎,如何落實以地方發展需求為核心,在基礎教學外,倡議導入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課程設計、推動產學合作、大學跨校互助、建立長設互助機制。
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使學生在畢業前就可得到校外專案實習、參與、學習與啟發的機會;可以透過地方發展需求帶動教學創新,讓台灣各縣都有特色大學。然後進一步,可以使各特色大學能為地方發展所用,成為可資仰賴的智庫、實習所與教育訓練中心。像這樣,朝著打造台灣自有的「國家創新系統」脈絡想去,一條具共識共行的大道昭然若揭!